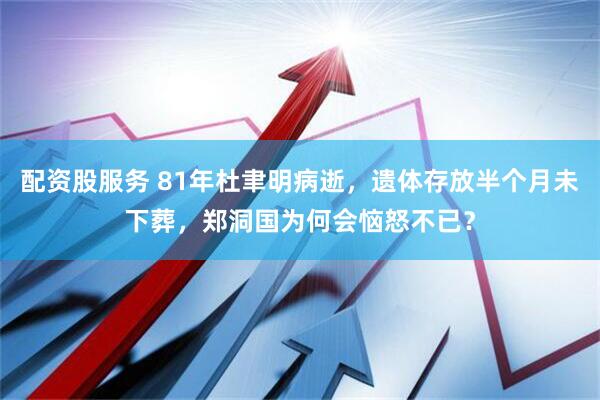
“1981年3月12日下午两点,老杜真的走了?”门房老兵压低了声音,摘下风帽,沉声应了一句:“嗯,他走得很安静。”短短对话,标记着西北军旧部相交半个世纪的终点配资股服务,也揭开了一段颇为尴尬的吊唁风波。
杜聿明离世,当年陪他一同被俘、又一同获特赦的郑洞国理所当然要张罗后事。照规矩,遗体在协和医院旁的小灵堂停留三天便可火化下葬,可清点名单时郑洞国皱起了眉:杜家的三个子女,一个在台北、一个在高雄、一个随女婿在美国,全都来不了。家人缺席,棺盖怎么合得上?郑洞国当场拍板——灵柩暂不动,等消息。
这一等就是十五天。高干病房里用的是进口冷柜,温度低、保存条件好,医务处倒没意见,只是礼仪部门连声催——春分前必定要火化,否则手续全乱套。郑洞国给台湾先后打了四次长途,每次都卡在同一环节:入台证件出不来。蒋经国办公室的回复很冷,“政治因素复杂,恕难照顾。”话语客气,却凉到骨子里。

再说生前与台北当局并无恶言,反倒多次写信要求团聚子女;可在岛内强硬氛围下,这种愿望被视为“可能被统战的陷阱”。儿女们想回来,也被“暂缓审批”堵在门口。郑洞国火了,直接在电话里丢下一句:“这是人情,不是政令!”然后摔筒,却换来忙音。
郑、杜两家交情深厚,源自黄埔一期。抗战时,郑洞国在长沙会战前线,两人并肩挖壕;淮海战役被俘后,又同在上饶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。1959年特赦时,二人一起走出劳改农场,郑洞国调军事科学院写史料,杜聿明留在政协搞文史,私下常聚,喝茶论剑。彼此了解,所以郑洞国心气冲:兄弟一辈子替蒋介石效死力,落到头来连最后一面都见不着?
这口怨气越积越重。守灵第四天夜里,他握着香烟嘟囔:“老蒋用人卸磨杀驴也就罢了,连一点体面都不留,这是欺负咱们没脾气。”旁边的护理员劝他休息,他摆手:“老杜怕冷,我不能走。”
与此同时,大陆方面给足了礼遇。中央统战部送来花圈,朱德元帅生前题赠的“化干戈为玉帛”被请到灵堂正前;军队老战友——许世友、陈赓的家人、粟裕之子——轮番吊唁。军乐团演奏的是《今夜无人入睡》,哀而不伤,多数来宾红了眼。

有意思的是,香港多家报纸第一时间刊出讣告,标题竟用了“国民党第一战俘将军圆寂”。措辞耐人寻味:既点出历史身份,也隐含时代和解意味。但台湾“中央社”却用了冷处理,仅仅一条短讯提到“杜某病故北京”。这种对比,更刺激郑洞国腹中闷火。
整整半个月后,眼见手续仍无进展,北京市委决定:先行火化,骨灰日后再由家人认领。郑洞国在追悼会上发言,没稿子,开口就是一句陕北方言:“老杜,我对不住你,没把娃们接回来!”说罢失声,满场皆默。几分钟后,老人拄着拐杖走到灵柩旁,狠狠敬了一个脱帽礼,声音沙哑,“这帐,总要算!”
按理说,军人去世,怒气不应在公众场合发作,可郑洞国的动怒,并不只是私人情感。他看得明白:三十年隔绝,让割裂成了习惯,而普通亲情成了政治筹码。1979年以后,两岸才刚刚试水通邮探亲,尚未铺开;杜聿明是“战犯”出身,更被台北列入“管制黑名单”。此事碰上政策空档,恰反映了那一时期的尴尬转型。

说点题外话,杜聿明自己倒想得开。生前与友人对弈,总自嘲“我这一子早被对面吃了,现在不过做劫”。他曾把《孙子兵法》与改造心得混写成笔记,留下十六字:审时度势,生死无惧;知恩图报,身后勿扰。郑洞国却性情更刚,凡事不肯忍。有人回忆,同批特赦的劝他看开些,郑洞国直说:“人生一口气,佛也难劝!”
这股子秉直,贯穿他和蒋介石交往的全过程。早在抗战末期,他就因质疑常凯申“抢收美援物资”吃过穿小鞋;来台曾被边缘化,后来干脆留在大陆。杜聿明不同,他入狱前对蒋还是死心塌地。正因如此,杜去世后被“冷淡对待”,郑洞国才格外不服,“有恩必报”本是行伍规矩,怎的到了政治层面就失灵?
火化前最后一刻,殡仪馆里只放亲友八十余名,其中四分之一是杜聿明在管理所结识的“老战犯”同窗——王叔铭、沈醉、都来了,面色沉稳。他们看着骨灰盒进炉,几乎异口同声念了一句:“走好。”那一瞬,谁也没说起往昔烽火,反倒聊起了杜所写的国画《寒梅图》,挂在政协走廊的那幅。有人轻声说:“老杜的梅,冷里带香。”说者无意,听者含泪。
半个月风波过后,郑洞国并未收敛情绪。他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,直接寄往台北,质问当年承诺“善待将帅家属”的蒋经国。信件自然石沉大海,他却把复写稿夹进回忆录。多年后,史学者翻检档案时读到这封信,仍能感到一股滚烫的怒意。

杜聿明的骨灰,最终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。一侧碑文是他亲笔写下的“忠诚报国”,另一侧则刻着曹秀清的名字。1984年,曹秀清长眠于旁,夫妻总算团聚。至于台北的子女,直到1989年两岸开放探亲后才第一次站在父母墓前,扶碑默立良久。郑洞国得知此事,淡淡说了句:“迟到,也好过没有。”
如果要给那场“半月停灵”找一个历史注脚,也许并不在于杜、郑二人身上,而在于那段时代对人情伦理造成的撕裂。试想一下,一位叱咤风云的兵团司令,最后竟要靠朋友据理力争才能维护体面,这本身就说明:即便烽火散去,战争的阴影还在,仍能束缚亲人之间一次简单的告别。
细细数来,风波已经过去四十多年。当年的执念或已淡化,但郑洞国当众拍桌的那一声怒斥,却依旧让后人感到刺耳又真实。情义、尊严、政治博弈,被浓缩在停灵室的短短半月,这才是历史最不经意的锋利之处。
牛股网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